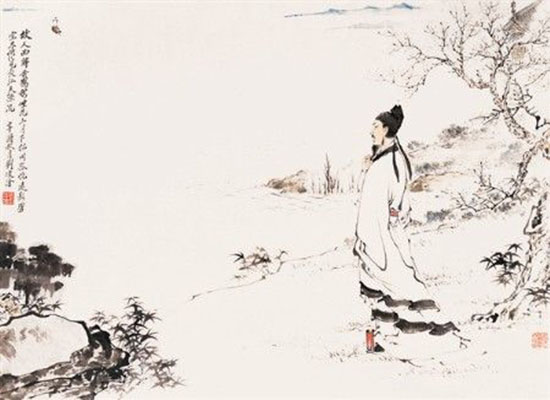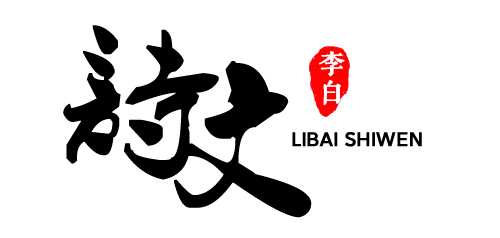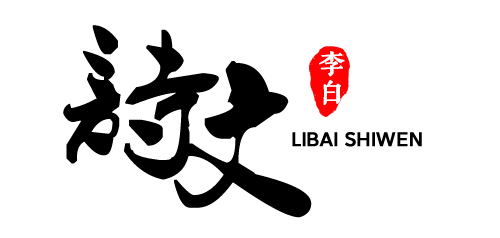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句别解
吴泓 周格丽
(青海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)
翻阅高中语文第六册课本及《教学参考书》,对李白《行路难》结句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理解,基本一致。课本注“意思是说自己一定会排除困难,实现远大理想。”而教参则将结尾两句合而析之:“(诗人)想到古人,坚信总有一天,象宗悫那样‘乘长风破万里浪,……扬眉吐气,激昂青云,‘直挂云帆济沧海,。”认为结句“描绘出一幅海阔天高,云帆万里的壮丽图景,用以寄托诗人的希望。”此种析解,亦多见于今版的诗选、赏析诸书,如: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《历代诗歌选》注:“‘‘长风’二句,是说自己定会乘风破浪,排除困难,实现埋想。”上海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古代文学读本》说明:“诗人却相信终有一天将乘长风破万里浪,渡过大海,直达理想的彼岸。”
笔者以为,“二句联解,抵捂颇多。
按:“沧海”乃道教传说中的海岛名,旧题东方朔《海内十洲记》记载:“沧海岛在北海中,地方三千里,去岸二十一万里,海四面绕岛,各广五千里。水皆苍色,仙人谓之沧海也。”《十洲记》虽系伪托东方朔之名而作,但汉代民间传说中,东方朔就已被人们塑造成一个长寿神仙的道者。
据《博物志》载:“汉武帝祭祀名山大泽,以求神仙之道。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,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。……时东方朔窃以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,母顾之,谓帝曰:‘此窥牖小儿夕尝三来盗吾桃。’帝乃大怪之。由此,世人谓东方朔神仙也。”
而作为一位素有“济苍生,安社稷”之大志,一生都要“申管婴之谈,谋帝王之术”的诗人李白,其诗作中也不时提及这位“偷桃之神”,如“愿同西王母,下顾东方朔,紫书倘可传,铭骨誓相学”(《赠嵩山焦练师并序》),“仙人东方生,浩荡弄云海。沛然乘天游,独往失所在”(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》),即便被“赐金还山”还以之自况:“世人不识东方朔,大隐金门是滴仙……君王虽爱蛾眉好,无奈宫中妒杀人”(《玉壶吟》)。
因此,诗人在《行路难》结句高唱出《十洲记》中的“沧海”仙岛,自然不应理解为“实现远大理想”、“继续追求光明”、“寄托诗人的希望”,而是诗人逐出长安,理想破灭,充满了悲观失望之后的一种精神上的暂时的自我解脱和宽慰,反映了诗人屏弃尘世,超脱现实的高蹈忘机的出世思想。
诗人以远涉“沧海”表弃世寻仙之意在他后期诗作中亦多有反映。“却顾海客扬云帆,便欲因之向溟渤”(《山水壁画歌》),“时命乃大谬,弃之海上行”(《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)及“灭虏不言功,飘然陟方壶。惟有安期舄,留之沧海隅”(《书怀重寄张相公》),而“一鹤东飞过沧海,放心散漫知何在”(《怀仙歌》),则更是诗人想象自己如单身只影的仙鹤鸟,栖身于浩渺烟波的“沧海”仙鸟。之所以这样说,我们还可以从《行路难》三首组诗的分析得到进一步的证实。
第一首的开篇即显示出诗人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内心的苦闷抑郁、感情的激荡变化和精神上的无法解脱,“闲来垂钓碧溪上,忽复乘舟梦日边”,亦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妄想。现实残酷,济世塞途,不得不唱出“行路难”的悲声,结尾二句道出了在封建社会,知识分子的两条出路一一或仕或隐。《行路难》三首反复咏叹的正是这种无法排遣的歧路仿徨,终归于隐的思想主题。为何仕途不通,终归“沧海”呢?
第二首讲得很明白:原因是他不愿与斗鸡赌狗之徒同流合污,表明了他在宫廷里倍受冷落、侮辱和嫉妒,感叹世无贤君圣主而归结于“归去来兮”。
第三首批评许由、伯夷、叔齐之流的沽名钓名,以伍员、屈原、陆机、李斯诸人丧身的故事表明了现实社会的黑暗与险恶,申诉了自己不得不辞官归隐的理由。
三首组诗,写来波澜起伏,充分反映出现实与理想无法调合的矛盾,而诗的结句皆以高蹈忘机(一以寻仙、二以归隐、三以纵酒)收束,这就不能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巧合,而是诗人理想破灭,对现实充满了悲观失望之后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,说明了诗人在组诗的立意构成上是同出机抒,远济“抢海”、归隐田园和纵情美酒,无不反映出诗人仕途失意后的出世的人生观。
至此,读者会问:结尾的前半句用宗悫少有大志之典,后半句又寓远济“沧海”归隐之意,前后是否矛盾?回答这个问题,我们应从李白与道教的关系上去考察。
我们知道,李白虽然从小就接受“道风”的熏陶,如“十五好游仙,仙游未曾歇.'(《感兴八首》),“五岳寻仙不辞远,一生好入名山游”(《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》)等。
然而事实上,在当时士人的心目中,道教信仰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,与其说是企望长生不死,得道成仙,不如说有其更深层的社会原因——未显时,以信道隐居为手段,抬高自我身价,走所谓的“终南捷径”以达到功名;失意时,既可表示对世俗的傲岸不谐,又可作为失去希望、理想泯灭以求另一种心理平衡的栖身之所。
李白亦未能免俗,据郁贤皓先生《李白丛考》考订: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曾在终南山隐居过,其时所作《赠裴十四》诗云:“身骑白鼋不敢度,金高南山买君顾。”“买君顾”即是想有朝一旧得到君王的重用,但此时的李白还是个影响不甚大的人物,隐居终南的目的在于玉真公主的别馆亦在此地,而玉真公主正是睿宗第十女,当朝天子唐玄宗的妹妹。她太极元年出家为道,后赐号持盈法师。
可见,李白隐居选择终南,确实是颇费一番心思的。由此,我们可以得出:李白信道具有其时代特性,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绝对的顶礼膜拜,诗人的主导思想是入世的,被逐出京,诗人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,这种矛盾和痛苦表现于诗中就显示出波澜起伏、激荡变化。结尾由前半句的入世思想转入后半句的出世的态度,正是这种变化、起伏的具体体现。诗人要施展抱负,实现理想,然而现实黑暗,仕途艰难,瞬即归结到出世的结局,而出世亦不失为失意之后一剂抚慰心灵创伤的妙药良方。
李白辞官作《行路难》不久,与杜甫同游梁宋,杜甫作《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》诗云:“不愿论簪笏,悠悠沧海情”,也可看作这位忘年之交对此时处于矛盾之中的李白的一种劝慰。稍后,诗人东之齐鲁,遇狄博通所作:“去年别我向何处,有人传道游江东。谓言挂席度沧海,却来应是无长风。”(《东鲁见狄博通》),诗表面似写挚友,实乃自况,更说明了诗人要归隐访道的真正缘由:我为何要远济仙岛“沧海”啊,不正是因为仕途受阻、宦海沉浮、世道艰难吗?如果说诗人在写《行路难》时正处于一种矛盾,仿徨,左右为难的心境之中,此时此刻,这种矛盾的心境已消失殆尽了。至此,短短的十四字的结句所表现的如此复杂的思想感情,如此丰富的社会内容,不也就涣然冰释了吗?